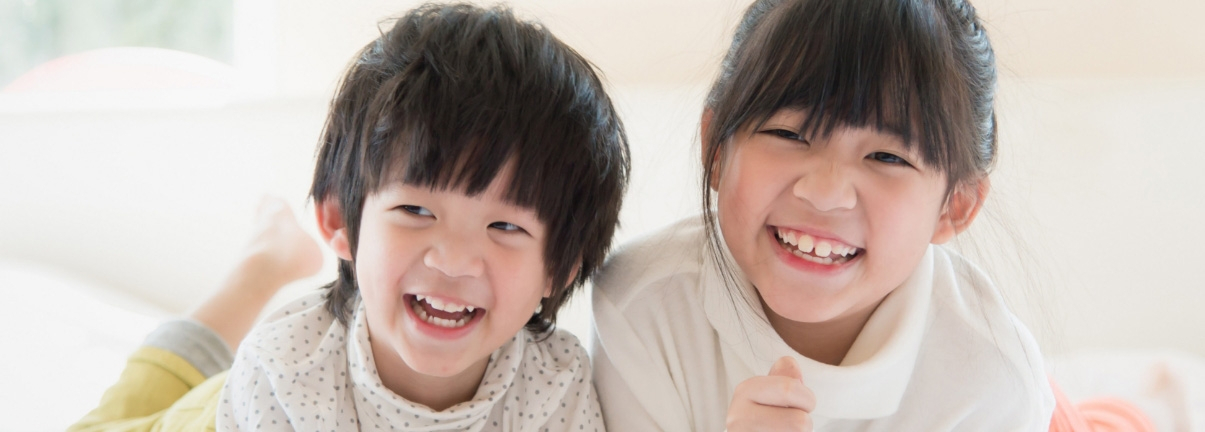23/12/2024
對守護兒童的認知與觀念調查研究
全港首個「守護兒童認知與觀念」調查
逾75%公眾對「守護兒童」缺乏認知 必須加強宣傳教育並為兒童相關企業員工提供培訓
香港保護兒童會(下稱「本會」)以「守護兒童」為機構核心文化,相信幸福的社會必須建基於一個孩子備受愛護和尊重、能夠健康成長,擁有快樂童年的環境。「守護兒童」是指實施全面措施和政策,保護兒童免受傷害、虐待、忽視和剝削,包括為兒童提供安全和有利的處境,並維護他們的權益。「守護兒童」涉及不同持份者,包括家長、照顧者、學校、社會各界組織和政府,唯有這些持份者共同努力,方能創造促進兒童健康成長的大環境。
過去兩年,本會除了制定並在轄下 27 個服務單位全面推行「守護兒童政策」外,更為全體員工、義工和承辦商等提供相關培訓,同時關注社會整體對守護兒童概念的認識和支持。為了解香港公衆人士和服務兒童的企業在守護兒童方面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本會委託社會政策研究有限公司 (下稱「社會政策」)進行全港首個「守護兒童認知與觀念」問卷調查。社會政策於今年 5 月 20 日至 7月 3 日期間,成功以電話訪問了 1,000 名 18 歲以上的公眾人士,並以網上問卷和面談形式訪問了400 名在兒童娛樂和休閒服務行業(下稱「兒童相關行業」)工作的職員,合共收集了 1,400 份有效回應。
主要調查結果
(一)75%受訪公眾對「守護兒童」缺乏認知;近 70%在兒童相關行業工作的受訪者對「守護兒童」這概念的了解也偏低。
(二)62%在兒童相關行業工作的受訪員工表示,其企業沒有或他們不知道其企業有沒有守護兒童政策;65%受訪員工同意,設有守護兒童政策對兒童會有更大保障。
(三)在受訪員工當中,71%沒有接受過「守護兒童」的相關培訓;而有接受過培訓的員工當中,超過 91%認為培訓對他們的日常工作有幫助。近 7 成受訪員工認為,企業有需要加強有關「守護兒童」的員工培訓和意識。
(四)公眾對立法會今年 7 月通過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的認知不高:42.5%兒童相關行業受訪員工曾聽聞此法例,而曾聽聞此法例的受訪公眾則只有 37.5%。大多數受訪者支持這項立法,認為提供了法律基礎,鼓勵專業人士舉報懷疑虐待兒童事件。然而,少數受訪者表達了保留意見,擔心法例被濫用。
(五)僅 37%與兒童相關行業的企業員工在入職前有進行《性罪行定罪記錄查核》,情況令人關注。
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周舜宜表示:「綜觀調查結果,我們認為有需要積極提高公眾,尤其是父母及照顧者對守護兒童的認知和理解;亦有需要鼓勵兒童相關行業的企業制訂守護兒童政策,訂定明確的行為守則和處理懷疑虐兒事件的程序指引,並為員工提供適當培訓。政府可以考慮設立兒童友善場所認證及嘉許計劃,讓公眾識別具備兒童友善設施的場所,同時鼓勵企業提升和增加兒童友善設施。在強制舉報方面,建議政府經常提醒公眾虐兒帶來的嚴重後果及法律責任,繼續推動宣傳教育工作。」
詳細建議
(一)加強「守護兒童」的意識和教育
進行具針對性的公眾教育和社交媒體推廣,以強調守護兒童的重要性,加深公眾和兒童相關行業職員對守護兒童的認識,尤其需要提升父母及照顧者對守護兒童的認知和理解。
(二)制訂明確政策及指引
鼓勵兒童相關行業的企業制訂守護兒童政策,並在招聘時進行有需要的背景篩查,提供明確的行為守則和處理懷疑虐兒事件的程序指引,強化企業員工在守護兒童方面的角色和能力。
保會於 2022 年 12 月率先推行《守護兒童政策》,內容包括行為守則、舉報政策、處理懷疑虐兒個案程序及守護兒童風險評估等範疇,政策已於保會全部 27 個服務單位實施,是保會過去兩年大刀闊斧改革的主要舉措之一。保會這份《守護兒童政策》可為其他服務兒童的機構和企業提供參考,有助他們制訂自己的守護兒童政策。
(三)提供培訓與專業發展機會
與兒童相關行業的企業應該為員工提供持續培訓,提高員工的警覺性,有效保障所服務兒童的身心安全和健康。
保會於 2023 年初成立「守護兒童學院」,為所有員工以至業界提供系統化及全面的專業培訓和支援,並設立「守護兒童專線」,由專業社工解答各種有關守護兒童的疑問,為保會員工及公眾提供諮詢服務。
(四)設立兒童友善場所認證及嘉許計劃
建議政府設立兒童友善場所認證及嘉許計劃,方便市民識別兒童友善場所,藉此推動相關企業提升及改善場所設施,營造有利兒童健康快樂成長的社會環境。
(五)立法規定執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政府應立法規定所有兒童相關行業的員工必須進行性罪行定罪記錄查核,加強篩查他們的性犯罪背景資料,並加快擴展機制覆蓋的人員類別和行業範圍。
完
----------------------------------------------------------------------------------------------------------------
資料下載: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1XaExWjJ7As-6b8BeQLcF6EHXLJmBJDf